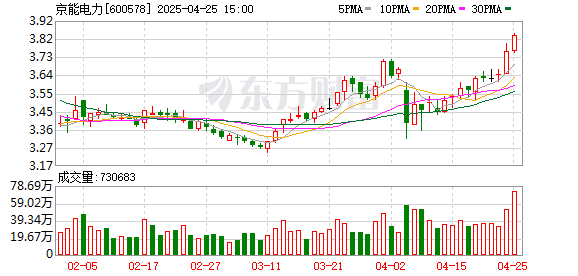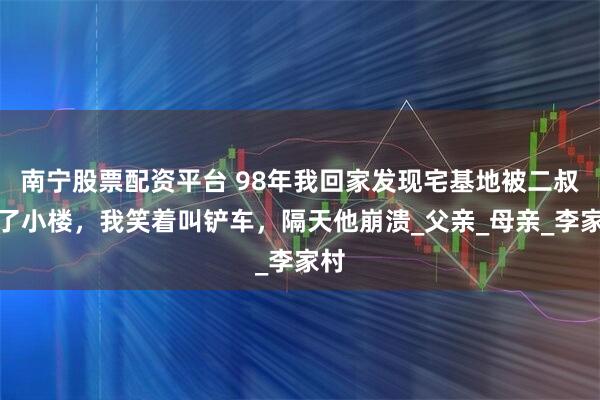
01南宁股票配资平台
1998年的夏天,燥热的蝉鸣像是要把整个村庄给点燃。我叫李建国,那年我二十六岁,揣着八年来在城里打拼攒下的所有积蓄,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——李家村。
李家村,一个坐落在群山之间的小村落,贫穷和落后是它撕不掉的标签。而我,曾经也是这片贫瘠土地上最不起眼的一粒尘埃。
我的童年,是在父亲无奈的叹息和二叔李建军的嚣张跋扈中度过的。父亲李建业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,一辈子信奉“吃亏是福”、“兄弟情深”。他和我二叔是亲兄弟,可性格却南辕北辙。二叔李建军,是村里出了名的无赖,游手好闲,偷奸耍滑,占便宜没够。
记忆里,二叔总是以各种借口来我家借钱、借粮。那时候家里也穷,父亲总是把为数不多的口粮分一半给二叔,把准备给我买新衣服的钱塞到二叔手里。母亲为此没少跟父亲吵架,可父亲总是一句话:“他是我亲弟弟,我不帮他谁帮他?”
展开剩余92%然而,父亲的善良换来的不是二叔的感恩,而是变本加厉的索取。我十岁那年,二叔说要做生意,信誓旦旦地找父亲借了五百块钱。五百块,在那个年代对于我们这样的家庭来说,不啻于一笔天文数字,那是父母亲面朝黄土背朝天,一滴汗一滴汗摔出来的血汗钱。父亲咬着牙,把家里准备翻新房顶的钱给了他。结果,二叔的“生意”没做成,钱也打了水漂。父亲去要过几次,二叔要么说没钱,要么就躺在地上撒泼打滚,骂我父亲不顾兄弟情分,逼他去死。几次三番下来,父亲也寒了心,那五百块钱最终不了了之,成了我们家一块说不出口的伤疤。
这还不是全部。村里分地,二叔总要耍赖多占一些,今天说我家的地界碑被雨水冲歪了,明天说他家的牛吃了我家的庄稼是我家没看管好。我家那头老黄牛,是父亲的宝贝,有一年冬天,二叔家没柴火了,竟然半夜三更偷偷跑到我家牛棚,把牛棚的木栏杆给拆了回去烧火,害得老黄牛在外面冻了一夜,差点冻死。
父亲气得浑身发抖,第一次抄起扁担要去跟二叔拼命,最后还是被母亲和村里的长辈死死拉住。他们都劝父亲:“建业,算了,他再浑,也是你弟弟,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啊。”
父亲最终还是放下了扁担,一个人蹲在院子里,抽了一整夜的旱烟。那佝偻的背影,和缭绕的烟雾,成了我记忆中无法抹去的悲凉。
我恨二叔,从我记事起就恨。我恨他的无赖,恨他的自私,更恨他一次次消费着父亲的善良。我曾不止一次地对父亲说:“爸,二叔就是个喂不熟的白眼狼,你不能再这么纵容他了!”
父亲只是摸着我的头,长长地叹气:“建国,记住,我们李家的根在这里,亲情是断不了的。人活一世,不能把事做绝了。”
父亲的“不能做绝”,却成了二叔得寸进尺的底气。
直到八年前,父亲积劳成疾,撒手人寰。临终前,他把我叫到床前,颤抖着从枕头底下摸出一本泛黄的宅基地证,交到我手里。
“建国,这是咱家最后一点家当了……爹没本事,给你留不下金山银山,就剩下这块地了……以后,你就在这块地上盖个大房子,娶个好媳妇,好好过日子,别像我……咳咳……”
我握着那本沉甸甸的证,泪如雨下。这是父亲留给我唯一的念想,也是我们家在这世上最后的根。
安葬了父亲,我看着空荡荡的茅草屋,和那片长满荒草的宅基地,心里一片茫然。我没钱,别说盖大房子,就连修缮一下这摇摇欲坠的祖屋都做不到。二叔倒是“好心”地过来劝我:“建国啊,你看你一个人,守着这破房子有啥用?不如把这宅基地卖给我,二叔给你两百块钱,你拿着去城里闯闯,也比在这穷山沟里饿死强。”
我看着他那张虚伪的脸,心中一阵恶寒。我爹尸骨未寒,他就惦记上我们家最后这点东西了。
我冷冷地拒绝了他。我知道,我若真的走了,这块地,这个家,就真的会被他吞得渣都不剩。
可是,留下来又能怎样?守着一块盖不起房子的地,守着一座随时会塌的茅草屋,就能改变命运吗?
那个夜晚,我在父亲的坟前跪了一夜。第二天,天蒙蒙亮,我背上行囊,揣着母亲留下的几件旧衣服和那本宅基地证,毅然决然地离开了李家村。我对自己发誓,不混出个人样,我绝不回来!我要让所有看不起我的人都看看,我李建国不是任人拿捏的软柿子!
02
城市的繁华,像一个巨大的漩涡,几乎要将我这个从山沟里出来的穷小子吞噬。初到城里,我举目无亲,身无分文,只能从最苦最累的建筑工地干起。
搬砖、扛水泥、和泥浆……每天累得像条死狗,躺在工棚的硬板床上,浑身的骨头都像是散了架。工友们看我年纪小,又肯吃苦,都愿意帮我一把。工头老张是个实在人,见我干活利索,脑子也灵活,便开始有意识地教我看图纸,学技术。
那段日子,白天我在工地上挥汗如雨,晚上我就着昏暗的灯光,啃那些比砖头还厚的建筑图纸和力学书籍。我知道,光有力气是没用的,我必须要有自己的本事。我把每一分钱都掰成两半花,一半寄回家给年迈的母亲,一半用来买书、报学习班。
别人休息的时候在打牌喝酒,我在学习;别人生病的时候在呻吟抱怨,我在咬牙坚持。因为我心里憋着一股劲,一股不服输的劲。我时常会想起二叔那副轻蔑的嘴脸,想起父亲临终前不甘的眼神。它们像鞭子一样,狠狠地抽打着我,让我不敢有丝毫的懈怠。
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。三年后,因为一次意外,工地的技术员摔伤了腿,一个紧急的项目图纸出了问题,没人能解决。我凭着自学的知识,硬是熬了两个通宵,把图纸给修正了过来,避免了公司巨大的损失。
这件事让公司的老板对我刮目相看。他把我从工地调到了技术部,我的命运,从那一刻开始,迎来了转机。
又过了五年,凭借着在技术部积累的经验和人脉,以及这些年省吃俭用攒下的第一桶金,我辞职了。我成立了自己的小型建筑公司。
创业的艰辛,比在工地上搬砖还要磨人。拉业务,跑关系,垫资金,每一个环节都可能让我万劫不复。最难的时候,我连员工的工资都发不出来,只能厚着脸皮去求以前的朋友帮忙周转。有好几次,我站在深夜的立交桥上,看着下面川流不息的车河,真想就这么一跃而下,一了百了。
可我不能。我一闭上眼,就是父亲那张布满皱纹的脸。他说,建国,好好过日子。
我挺了过来。靠着过硬的工程质量和诚信的口碑,我的公司慢慢在城市里站稳了脚跟,从小项目做起,一步步发展壮大。到1998年,我的公司已经颇具规模,在业界也有了一定的名气。
我终于有钱了。我不再是那个连房子都盖不起的穷小子了。
八年了,整整八年,我没有回过一次家。不是不想,是不敢。我怕看到那片荒芜的宅基地,怕面对自己无能为力的窘境。现在,我终于可以挺直腰板,衣锦还乡了。
我要在父亲留给我的那块宅基地上,盖一栋全村最漂亮、最气派的小楼。我要让父亲在天之灵看到,他的儿子,没有让他失望。我要让所有曾经看不起我们家的人都知道,三十年河东,三十年河西,莫欺少年穷!
03
回乡的路,既熟悉又陌生。车子在颠簸的土路上行驶,窗外的景象渐渐从高楼大厦变成了低矮的平房和连绵的青山。空气中弥漫着泥土和庄稼的气息,这是我离别了八年的故乡的味道。
我的心情是复杂的,既有近乡情怯的紧张,也有一雪前耻的激动。我在脑海中构思着新房子的蓝图,两层的小洋楼,带一个大大的院子,院子里要种上父亲最喜欢的桂花树。
然而,当车子缓缓驶入李家村的村口时,我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了。
远远地,在我记忆中那片属于我家的宅基地的位置上,赫然耸立着一栋崭新的两层小楼!
那楼房刷着白色的墙漆,贴着时髦的瓷砖,在周围一片低矮破旧的土坯房中,显得格外扎眼。
怎么回事?
我的心猛地一沉,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。难道是我记错了位置?不可能!那块地,那棵歪脖子老槐树,化成灰我都认得!
我让司机停车,快步向那栋小楼走去。越走近,我的心就越凉。没错,就是这里,这里就是我家的宅基地!
此时,小楼的院门“吱呀”一声开了,一个熟悉又令我厌恶的身影走了出来。他穿着一件崭新的夹克,挺着个啤酒肚,嘴里叼着烟,一脸的得意和满足。
是二叔,李建军!
他看到我,先是一愣,随即脸上堆起了虚伪的笑容:“哎哟,这不是建国吗?什么时候回来的?发大财了啊,都坐上小轿车了。”
他的目光在我的车上扫来扫去,充满了贪婪和嫉妒。
我没有理会他的寒暄,指着他身后那栋刺眼的小楼,声音因为愤怒而有些颤抖:“二叔,这房子是怎么回事?”
二叔闻言,脸上的笑容僵了一下,但立刻又恢复了那副无赖的嘴脸。他弹了弹烟灰,满不在乎地说道:“哦,你说这房子啊。建的呗。你看,你这孩子也是,一走就是八年,音信全无。这宅基地空着也是空着,长满了荒草,多浪费啊。我寻思着,反正你也不回来了,我就帮你给利用起来了。怎么样,二叔盖的这房子,气派吧?”
他语气里的那份理所当然,像一把淬了毒的尖刀,狠狠地插进了我的心脏。
“我不回来,这地就成你的了?!”我气得浑身发抖,“李建军,你还要不要脸!这是我爸留给我的宅基地!房产证上写的是我李建国的名字!”
哎,话不能这么说嘛。”二叔把烟头往地上一扔,用脚碾了碾,吊儿郎当地说,“什么你的我的,咱们都是一家人,分那么清楚干嘛?再说了,你爹活着的时候,就属我跟他关系最好。他要是泉下有知,知道我住上了这么好的房子,肯定也替我高兴。”
“你放屁!”我再也抑制不住胸中的怒火,破口大骂,“我爸怎么死的你心里没数吗?要不是你一次次把他当冤大-头,他能积劳成疾那么早走吗?你现在还有脸提他!”
我的怒吼引来了不少村民的围观。他们对着我们指指点点,议论纷纷。
二叔的脸上一阵红一阵白,被我当众揭了老底,有些挂不住了。他眼珠子一转,索性耍起了横:“李建国!你小子别给脸不要脸!你现在有钱了,出息了,就回村里来跟我耍威风了?我告诉你,这房子我已经盖了,住也住了,你还想怎么样?有本事你把它拆了啊!”
他双手叉腰,一副“你奈我何”的无赖模样。
“你别以为我不敢!”我死死地盯着他,牙齿咬得咯咯作响。
“你敢?你拆一个试试!”二叔挺着脖子吼道,“这房子可是花了我大半辈子的积蓄!你要是敢动一砖一瓦,我就……我就一头撞死在你面前,让你背上一条人命!”
看着他这副撒泼打滚的架势,我仿佛又看到了当年那个躺在地上赖掉父亲五百块钱的他。这么多年过去了,他一点都没变,还是那么的无耻,那么的不可理喻。
跟这样的无赖,讲道理是行不通的。任何的言语,在他面前都显得苍白无力。
周围的村民也开始七嘴八舌地劝说起来。
“建国啊,算了吧,毕竟是你二叔。”
“是啊,房子都盖起来了,拆了多可惜啊。”
“一家人,有什么事不能好好商量呢?”
这些“和事佬”们的劝说,听在我耳朵里,只觉得无比刺耳。他们站着说话不腰疼,被侵占的不是他们的土地,被欺负的不是他们的家人。
我深吸一口气,强迫自己冷静下来。愤怒解决不了问题,只会让我陷入被动。
我看着二叔那张得意的脸,心中忽然涌起一股冷笑。你以为盖起来了就成了你的吗?你以为耍无赖我就拿你没办法了吗?李建军,你太小看我李建国这八年在外面吃的苦,也太高估了你自己。
04
我没有再和他争辩。
在众人惊诧的目光中,我突然笑了。那笑容里,没有愤怒,只有彻骨的冰冷。
“好,很好。”我点了点头,看着二叔,一字一句地说道,“二叔,这房子你盖得确实不错。既然你这么喜欢,那就好好住着吧。”
说完,我转过身,径直回到了车上。
我的反应,让所有人都愣住了。二叔显然也没想到我会这么轻易就“认怂”了。他站在原地,看着我绝尘而去的汽车,脸上露出了胜利者般的得意笑容。在他看来,我不过是虚张声势,雷声大雨点小。毕竟,谁会真的为了争一口气,去拆一栋已经建好的房子呢?那可是白花花的银子!
车上,司机老王透过后视镜看了看我,小心翼翼地问:“李总,就……就这么算了?”
我靠在座椅上,闭上眼睛,脑海里不断回想着刚才二叔嚣张的嘴脸,和父亲那张饱经风霜的脸。算了?怎么可能算了!
父亲的教诲是“不能把事做绝”,但前提是对方得是个人。对于二叔这种连亲兄弟的骨头都要啃的畜生,任何的忍让和退步,都只会助长他的气焰。
八年前,我没钱没势,只能选择远走他乡。但今天,我已经不是那个任人欺凌的穷小子了。
“老王,”我睁开眼,眼神里一片平静,但平静之下,是即将爆发的火山,“掉头,回城里。另外,帮我联系几家靠谱的拆迁队。”
老王一愣,随即明白了我的意思,脸上闪过一丝惊讶,但很快就变成了然。他二话不说,猛打方向盘,车子在土路上划过一道漂亮的弧线,向着城里的方向疾驰而去。
回到城里,我立刻开始行动。我动用了自己公司所有的资源和人脉,一个下午的时间,就联系好了八辆大型铲车和配套的运输卡车。我还特意咨询了律师,确认了我的宅基地所有权的合法性,以及在我的土地上,我有权处理任何未经我允许的建筑。
一切准备就绪。
第二天,天刚蒙蒙亮。我知道,二叔有早起去镇上茶馆喝茶打牌的习惯,不到中午是不会回来的。
这个时间点,是最佳的行动时机。
我带着由八辆铲车和十几辆重型卡车组成的庞大车队,浩浩荡荡地再次杀回了李家村。
当这支钢铁巨兽般的队伍出现在宁静的村口时,整个李家村都被惊动了。早起下地干活的村民们纷纷停下了脚步,目瞪口呆地看着眼前这壮观的景象。他们交头接耳,议论纷纷,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大事。
我没有理会任何人,直接指挥车队开到了我家的宅基地前,将那栋碍眼的小楼团团围住。
我从车上下来,手里拿着那本被我珍藏了八年的宅基地证,以及城里律师事务所开具的法律意见书。村长闻讯赶来,看到这阵仗,吓得脸都白了。
“建国!建国你这是要干什么啊!使不得!使不得啊!”村长跑得上气不接下-气,拦在我面前。
我将手里的文件递给他,冷冷地说道:“村长,这是我家的宅基地证,具有法律效力。这栋房子,是李建军违法建造的侵占物。我现在,要依法收回我的土地,拆除这栋违章建筑。谁要是敢拦,就是妨碍司法公正,后果自负!”
我的话语铿锵有力,不带一丝感情。那冰冷的眼神和强大的气场,让原本还想上来劝说的几个长辈都望而却退。他们知道,今天的李建国,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可以任由他们用“亲情”和“辈分”来绑架的少年了。
村长看着文件,又看了看我身后那几台已经启动引擎,发出阵阵轰鸣的铲车,额头上渗出了冷汗。他知道,我是来真的了。
“所有师傅,”我拿起一个扩音喇叭,对着车队喊道,“给我听好了!把这栋房子,给我夷为平地!所有的建筑垃圾,一块砖都不要留在这里,全部给我运到它该去的地方!”
随着我一声令下南宁股票配资平台,八台铲车的巨大铁臂同时高高举起,然后,在所有村民惊恐的尖叫声
发布于:河南省益升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